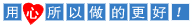1月14日上午10时,浙江省温州市殡仪馆8号告别厅。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王志杰此刻却安静地躺在火化炉前,孩子的亲人已是泣不成声。
“虽然舍不得,但这也是孩子生命延续的一种方法。”孩子的父亲王清林说,1月12日,面对救治无望的儿子,在医生的提议下,他们决定孩子身故后无偿捐献器官,“孩子火化了也是一无所有,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人。”
据了解,目前孩子的肝脏、肾脏已经让包括一个仅13个月大的小女孩在内的3名病人重获新生。年仅4岁半的王志杰由此成为温州首位儿童器官捐献者。
无疑,得到捐献的13个月大的小姑娘是幸运的,她遇到了王志杰一家人。
“近两年来,我国健全了器官捐献的程序、理清了组织架构,器官捐献是个特别严格谨慎的事情,在过程中需要第三方见证、死亡标准判定等等专业参与。”北京市人体器官捐献南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王璐说。
“以前,我国器官来源主要有死囚器官捐献、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三条途径。死囚器官捐献由于有悖于世界普遍接受的伦理学原则,会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由于会对捐献者造成创伤和健康隐患,同时也滋生伪造亲属关系的器官买卖市场,这一渠道也不宜提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解决器官来源的最佳途径。”北京大学医药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介绍说。
王璐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北京市每天都有患者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的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器官来源的严重匮乏成为制约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自2011年3月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以来,至2012年年底,38个试点单位完成人体器官捐献500例,北京完成第一例已是2012年12月底。虽然在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王璐说,造成“太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北京市为例,很多到我们这里表示愿意捐献器官的志愿者是不符合标准的,只有在60岁以下、原发病为脑部疾病、身体器官条件较好的志愿者是合格的,除此之外比如说癌症患者等都是不可以的。另外,涉及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的捐献者我们也是不接受的。”王璐说,“我国的捐献一定是自愿无偿的。我们也接到过电话,说‘我要卖个肾’,这属于非法行为。”
在王岳看来,“太少”的背后是供体渠道的“不畅通”以及立法体系的缺失。2007年5月1日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里程碑式的立法,“条例实施之后,非血亲、姻亲以及收养关系的活体器官移植手术被基本叫停,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证明存在因亲情而帮扶的人员之间。但是,在叫停以前混乱的活体器官捐献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打开供体提供的渠道”。
“我国器官捐献、移植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全面、不完善,离建立一套完整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仍差距较大。”王岳举例说,比如说器官移植离不开的脑死亡标准,“这方面在我国是空白状态”。
“当务之急,是建立完整的器官移植法律体系,而不是具体的一部法律法规。法律体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卫生部的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的协同等等。此外,我国还亟待建立生前器官捐献预嘱制度。这一系列是个系统工程。”王岳说,通俗讲也就是生前的意愿调查制度,“可以在换领第二代身份证或驾驶执照的时候,有关部门为此准备一个意愿调查表。我们曾就此在北京做过调查,市民对于此类调查还是很欢迎的,而且也愿意捐献器官”。
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王岳认为“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是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这就需要一个透明原则贯彻始终。由于目前器官捐献的尚不透明,造成一些人可以得到多个器官移植,有人在等待中死亡。”王岳说,从法律的角度,器官捐献、移植要求程序的正义,“由各地的红十字会或者血液中心建立一个透明的捐献器官的分配中枢,强调一个机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据悉,2011年,卫生部已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的器官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透明原则的实现,还需要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可以由所谓的政府职能延伸部门大包大揽。”王岳建议说,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可以用来确保透明。
“在有关部门组织架构、政策法规、捐献热线等一系列架子搭起来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宣传。”王璐向记者建议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专家卓小勤也向记者提出,目前传统观念阻滞的器官捐献需要有关部门以及全社会的大力宣传,“只有让百姓明白、了解器官移植,不让其有惧怕之心,才能向前推进其发展”。
“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前进之路,单靠‘堵’是不可以的,要大量透明地增加供体的数量,要疏导。”(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