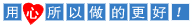医药网6月12日讯 “要想富,干介入。”不同的人会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
医学生可能将它视为学科受欢迎指南,心血管病人可能将它当作医生人品的试金石,而医学专家、媒体公众则从中嗅到过度医疗的信号。
日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博士生举报导师杨向军乱装支架并收回扣。有关心脏支架的探讨再次火热。
“成本两百多,暴利三四万”,心脏支架真的是医生的摇钱树吗?人们对心脏支架滥用的担忧有根据吗?
支架手术已远超单纯医技范畴
2005年5月,宁波人林昊身体不适,一度连正常走路都有困难。林昊先后去了三家医院进行检查,都没能查出病因。
后来,在宁波市第一医院的心血管科检查时,医生告诉他,你来对地方了。林昊的一条冠状动脉堵塞较为严重,还有一条也有堵塞发生。医生建议,立刻安装心脏支架,以保证正常供血。
心脏支架又称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这根1-3厘米左右的空心、可伸缩的导管,能够撑开硬化、狭窄的心脏冠状动脉,保持心肌肉血流灌注。
从第一例心脏支架介入手术至今,中国医学实践已经走过了35个年头。35年间,支架从金属的第一代发展到生物可吸收的第三代,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即俗称的支架手术数量激增。
根据国家卫健委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网络申报数据(包括网络直报数据及军队医院数据),近年来,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直接PCI的比例明显提升,直接PCI共55833例,比例达38.9%。手术指征及器械使用较为合理,介入治疗的死亡率稳定在较低水平,2016年为0.21%。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指具有典型的缺血性胸痛持续超过20分钟,血清心肌坏死标记物浓度升高并有动态演变,心电图具有典型的ST段抬高的一类急性心肌梗死。它主要由于冠脉斑块损伤诱发急性闭塞性血栓,急性患者发病12小时内推荐直接进行PCI。
林昊住院后三天进行了手术。当时,她和老伴在国产支架和进口支架中,选择了进口的。最后花费近三万元,她的冠脉里装上了一个支架。
不过让林昊老两口欣慰的是,没有在胸口开刀,只是在大腿处开刀,手术后伤口上只贴了个创可贴。术后不到十天,她就出院了。和她同期的病人,有的一次放了三四个支架。这让她觉得自己的病还没那么严重。
但在安装了支架后的三年内,林昊时不时还是感到胸口疼痛。每次因为这个原因就医时,医生都会让她住院观察两三天。这三年中,几乎每年她都要为此住上一两次院。
“说到底这个东西毕竟不是属于人自己的东西,放在心脏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尽管做心脏支架手术的人越来越多,但林昊还是觉得,在人体里放入这种外来的东西,即便是医学的进步,也还是让人担忧。
林昊的想法也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心脏支架手术后得终生服药”、“支架手术后血管还有可能堵塞”、“心脏支架没用,都是医生为了吃回扣放的”、“××家的××,放了十几个支架,还是没救过来,如果不放支架还能活久点”……这些真假不明的讨论,常常在日常生活中被当做常识,也成为一些自媒体鼓吹的“知识”。
事实上,我国支架手术平均单次置入数量是1.5个。在2018年4月21日第21届全国介入心脏病学论坛(CCIF)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介绍说,2017年,我国大陆地区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死亡率近几年整体稳定在较低水平,支架置入数稳定保持在1.5个左右,表明介入治疗指征及器械使用较为合理。(包括网络直报数据、省级质控中心核实后增加数据及军队医院数据)。
“现在医保对医院耗材管理很严格,不允许一次植入多枚支架。”东北某三甲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莉(化名)说。她坦言,心脏支架手术更多由主观因素决定,指南只是说明什么情况下支架手术更有益,并不具体。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不会有太大问题。
北京某三甲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李和平(化名)指出,从今年6月15日起,北京在取消药品加成后将进一步取消所有耗材加成。即便从最世俗的角度思考,从医院层面来说,放支架的经济收益也已不再存在,医院、科室层面没理由鼓励病人去进行支架手术。
“想从病人身上赚钱的大夫,干了一次两次,很快就会被看不起,就会被淘汰。”李和平说,主任医师在做决策的时候,也要受到主治医师、住院医的监督,“你能为了经济利益,去放弃所有支持你的这些人吗?”
但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则从社会和行业发展角度着眼,鲜明指出引入第三方监督是行业发展和保护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胡大一呼吁,支架本身是好技术,但它的使用已远超单纯的医疗技术范畴,衍生为一个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产业。
他最大的忧虑来自于目前的支架使用中,医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胡大一指出,关于支架过度使用的讨论中,坚持认为我国支架不存在过度使用者展示的数据“中国接受支架的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很少,同时承认支架获益最肯定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接受支架的比例很小,大多数支架患者被标记为不稳定性心绞痛或ACS。”
“谁在检审数据,如何核实数据?不实数据比无数据更可怕,更有害。”胡大一指出,数据由各单位医生自行填表上报,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他呼吁,通过公正公平公开的透明机制来管检支架的使用。
心脏支架被滥用了吗
李和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讨论是否滥用支架,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思考:一是是否不该放置支架而被放置支架。此种情况,如果医生诱导病人放置,则为滥用。二是不完全合乎指南的放置,也可以被称为滥用。李和平认为,后者是更为普遍的情况。“应该没有医生会在没有问题的血管里放支架。”
胡大一曾针对支架、心脏起搏器的风险表示了担忧。他指出,医生在患者血管里和体内放置了其不需要的金属异物,有的时候其病情非但没有减轻,还增加额外风险,如支架需“双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带来的出血风险,起搏器带来的感染,甚至败血症风险。胡大一担忧,过度医疗伤害患者,并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
心脏支架会在何种情况下遭滥用?胡大一曾发表观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是过度体检做冠状动脉CT,对一些CT发现斑块但没有临床症状的患者,不做有无心肌缺血的评估,直接冠状动脉造影,甚至冠状动脉内超声。只要最终狭窄大于等于、甚至小于70%就放支架。另外,众多稳定心绞痛的患者,被冠以不稳定性的诊疗,“被支架”,而这些患者往往被放置多个支架。
李和平就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心脏上放了13个支架。但这些支架并非一次放上,而是经历了5-10年,通过几次手术,陆续置入的。
张莉解释道,实践中单支架就能解决问题,但存在为了要求“完美”,植入两个或更多支架的情况。
“支架主要是为了改善供血,缓解病人症状。例如某个患者冠脉病变很多处,但最重的可能只有一处。单支架可以处理,但植入后其他病变可能看着就不好了,可能进行支架连接再植入。”张莉说,冠脉血管连着放支架,多数放不了十几枚,此种情况,基本是支架内又发生狭窄,继续植入的。
胡大一还提到一种情况,即病人供应心肌的冠状动脉主干道血管——左主干和多支血管多处病变,本应进行搭桥手术,也被放置支架。
李和平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确认了这一说法。他说,一些病人冠心病程度非常严重了,例如三支血管都有75%以上的狭窄,或合并糖尿病等,此时,按照支架指南,心脏内科大夫不应该放置支架,而应该交给心脏外科做搭桥手术。
张莉也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确认了这一现象并不少见。“有时候我们转诊给上级医院的病人,应该做搭桥手术的,回来发现还是做了支架手术。”
应该开胸搭桥的病人,为何最终选择做了支架手术?李和平和张莉发现,原因并非单一的。
李和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全国有能力做心脏外科手术的医院有700多家,而其中一半医院年手术量在50例以下。因此,并非所有病人都有条件在当地医院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除了医疗水平的因素,病人也在手术中参与决策。李和平也提到,目前相关标准要求,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在75%以上,才放置支架。但也有病人狭窄程度在60%多,也选择放置支架。此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病人和医生觉得病情会发展至75%以上。
李和平坦言,对于相当一部分病人来说,开胸手术听起来更为恐怖,更多人选择微创手术,以减少手术风险和恢复的成本。一些病人抱着大手术伤元气的传统观念,更倾向于不动刀子治病。但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支架的效果更小。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已经失去了搭桥手术的机会。
但医疗判断永远不是决策的唯一准则。在术前都会进行谈话,病人和家属只要有一方不同意,手术就不会进行。张莉说,除了这些原因,考虑到搭桥手术后如果出现问题,目前针对桥血管没有太好的处理方法,也是医生和病人纳入考量的因素。
心脏支架还不够 医疗资源有待下沉
“站在大夫角度讲,(我们)都觉得心脏支架力度是不够的。”李和平了解到,我国搭桥手术每年实施5万多例,而这一数字在美国超过30万。他指出,PCI角度也会有类似的对比。
但整体不够,就意味着不存在滥用吗?李和平指出,资源再有限,也不排除被用在无效治疗上的可能。
2016年6月19日,《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2016)》在沈阳东北心血管病论坛期间发布。这一指南由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韩雅玲牵头,113位国内心血管领域顶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共同完成。
这份指南建议,对于稳定性冠心病(SCAD)患者,将冠脉病变直径狭窄程度作为是否干预的决策依据,狭窄≥90%时可直接干预;当狭窄<90%时,应对有缺血证据或FFR≤0.8的病变进行干预。
李和平几年前就从相关学术文章中发现,美国支架手术中,绝对遵从指南的比例也不是特别高。该文章在解释这一数据时,也考虑到了医生的医疗判断在手术实施与否的决策过程中,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
让不少医生更为忧心的是,有关心脏支架滥用的不准确论调太过盛行,会影响到真正需要的病人。
社会上曾有一个常见的说法,目前一半的心脏支架都可以不用放。这一并不来自于调查也没有数据支撑的说法,也成为苏州博士生举报导师引起舆论关注的一条“佐证”。
“如果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被送到一个能很好地放置支架的医院去,想到这句话,他拒绝放支架了,那对病人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李和平对这种说法感到忧心。
一位心血管内科临床博士、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医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采访。她认为,卫健委的数据已经清晰证明了,当前支架手术绝非滥用,而是不足。对这个问题过多探讨,反而会引起“胡说派”的反对,对真正的病人不利。
霍勇在第二十一届CCIF上指出,血管疾病介入治疗病例数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情况仍然显著,分级质控势在必行。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病人来说,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在6个小时内放置支架。从这角度讲,我们的支架还远远不够。”李和平刚刚参加了一项有关我国心血管疾病住院死亡率的研究。他从数据中发现,不同地区的死亡率差异非常大。而这也是目前很难迅速得到解决的问题。
“国家卫健委也在做疾病治疗质量控制,一级一级下去,就是要寻找一些关键指标,来针对性地对每个医院进行评估,给予一些干预和培训,能够从能力层面提高医疗水平。”李和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