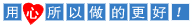医药网11月27日讯 昨天,来自中国深圳的贺建奎副教授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诞生了。这在全世界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激起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科学家们海啸般的讨论。
这样一个很可能是人类医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的临床试验,却在开始之前、进行之中从未见有任何报道和讨论,更没有看到任何严肃的科学论文。就像“放卫星”一样轻率地通过新媒体来报道。并且,在没有权威专家鉴定的情况下,自行宣布新生婴儿均为“健康”。
这让全世界严肃的科学研究人员们大吃一惊。通过基因技术来修改人类基因,除了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安全性外,也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社会伦理问题。除了科学界为此震惊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对本来具有“健康基因”的孩子因为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变得“命运堪忧”。因此,可以把这个事件称作基因编辑历史上的“伦理门”。
质疑1:
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为时尚早
人类基因组本身很可能并非是一个完美的体系。而具体到每个人的基因组,则更加可能带有各种致病基因。因此,在打开基因的密码后,通过基因修饰的方法来消除疾病隐患,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从原理上讲是可,并且也应该是生命科学界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科学界目前的共识认为,目前的技术,包括最为先进的CRISPR技术都不能保证准确无误地进行必要的基因编辑。因此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为时尚早。而这一点,贺教授本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2017年2月,贺教授参加了一次国际性的研讨会(据贺教授称这次会议是闭门会议)。但是会后,贺教授还是在他的博客里公开了自己的意见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14529&do=blog&id=1034671)。
在这篇科学网的博客里, 贺教授重点谈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科学界一直非常关注的CRISPR的“脱靶”(Off-Target)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优化sgRNA来避免或减少“脱靶”,但是很多人认为要做到完全不脱靶是不可能。去年六月份,在《自然方法学》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一个旨在修改失明小鼠模型中单核酸变异的CRISPR导致了1600个基因变异。因此,贺教授在他的博客中正确地指出,只有达到“很少或没有脱靶的人类胚胎才能成为可能”。
此外,他还提到目前基因编辑中的其他安全性问题,如发生基因“嵌合体”(Chimera)的问题,Cas9核酸酶和sgRNA如何影响胚胎发育的问题,以及进一步考虑基因编辑后的多代遗传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考量,贺教授认为“目前用于人类生殖目的基因编辑尚未解决科学上的安全性问题,尤其是脱靶和嵌合体。在解决好以下的安全性问题之前,进行人类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的”。
难道这样的难题在短短一年里就已经被攻克了吗?而且从时间上看,就在贺教授写下这段话的同时,这个违背他自己结论的临床已经在准备中,或者已经开始了。
质疑2:
人类胚胎研究的“14 天法则”
世界各国对于在人类胚胎中进行基因编辑都有着严格的管控。这些管控的目的并非“技术性”的,可以说是完全出自“伦理”方面的考量。这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胚胎可以被认为是有了“生命”。也许从宗教人士的观点来看,生命从受精卵开始。
但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以及考虑到早期胚胎的各种不确切性,这个时间段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些。中国科技部2003年的文件规定了关于人类胚胎研究的“14 天法则”:即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同时,也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
对此,贺教授也是完全清楚的。他在2017年的博客里强调体外培养的人类早期胚胎必须“遵守现有的14天规则”。 贺教授现在需要拿出充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的这次临床试验可以超越国家允许的14天规则?同时用充分的科学数据来说明这一次胚胎基因编辑的安全性。这并非是给国家监管部门和科学界的一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对这两个已经出生的新生命的责任。
质疑3:
关于这一项目的安全性保障,如何说服伦理委员会?
贺教授这次几乎获得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的临床试验,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Ethics Committee)管理方法严重的质疑。伦理委员会建立的目的是要防止临床医生在病人体内进行任何违反基本伦理的试验。正因为如此,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并不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士。按照规定,“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委员由设立该伦理委员会的部门或者机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从生物医学领域和管理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领域的专家中推荐产生”(https://baike.baidu.com/item/伦理委员会/8884401?fr=aladdin)。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当时伦理委员会讨论的记录,但是仅仅参考一下贺教授自己的这份博客,就很难想象他当时是如何向这样一个包含多方面人士的伦理委员会说明这一项目的安全性保障,而更难想象伦理委员会成员在贺教授做出的上述“在解决好安全性问题之前,进行人类生殖目的的基因编辑是不负责任的”结论情况下,又是如何批准这个世界上首次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试验的。
贺建逵是南科大的副教授,但他却选择在一家民营医院中通过伦理批准并开展临床。事实上,很多这种地方的“伦理委员会”已成为开展各种非正规临床的一张薄薄的纱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来发生的与临床试验有关的事件,从“魏则西”到最近的CAR-T治疗等,无不和目前这种近乎放任自流的机构本身“伦理委员会”批准方法有关。世界各国对医药临床严格的监管是用生命换来的结果。难道我们也还需要继续用生命来“交学费”吗?
至于把CCR5 而不是其他生命攸关的基因变异作为这次基因编辑的对象,已经有很多HIV专家指出其中的谬误。而曾经与贺教授同时参加2017年国际论坛的著名的美国基因编辑专家 George Church 教授也许看得更透。他说,”采用人类胚胎做试验说明研究人员的目的是在试验这个方法,而不是避免(孩子将来)得病。”(The use of that embryo suggests that the researchers’ main emphasis was on testing editing rather than avoiding this disease)
看来,贺教授需要面对很多人的质疑,而他未来最大的质疑者将会来自这两个刚刚出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