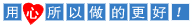自昨天人民网对「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的报道发出后,不到 24 小时,此事已经在全网发酵。
包括Nature及Science在内的国际顶级学术网站,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登上网站首页。
基因编辑婴儿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与这场巨大风暴的喧嚣不同,在 20 世纪之前,人们对于基因的力量,还处于屈服而束手无策的状态。
但就在短短百年之内,基因技术研究领域的高歌猛进,让人类与基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
现在,人类对于基因的研究与操作,不仅仅是探讨「能不能实现」的技术手段,更是对于「去不去触碰」的道德选择。
这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是人类与技术无限的缠斗,难以回头。
当我们整理、回顾这场人类与基因博弈的历史,其中反复交织着进步的狂喜与教训的伤痛,或许能为你带来一些关照目前事件的启发。
从摆脱疾病,到操控「完美」
在 20 世纪及其之前,在家族性疾病面前,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平等的。
人类对基因的巨大影响无可奈何,我们服从基因犹如服从命运。直白地说,人类不过是基因的奴隶。
但人类与基因之间的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巨变。
被认为是先天的基因可以被定位、分离、测序、合成、克隆和重组。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发生了互换,人类试图掌控基因。
就连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也曾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呢?」
如此一来,人类将不再是曾经的人类,人类将迈向「后人类时代」,疾病乃至死亡的威胁都将会被大大扫清。
然而,虽然科学进步有其客观标准可供参照,但科学与社会的交织和缠绕,却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
1930 年代,纳粹政权为实现对人类遗传的操控,在种族清洗时颁布《遗传病后裔防治法》。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遗传病患者(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都将接受外科绝育手术。
当时,英国、美国、德国、法国都存在浓厚的优生学观念。当时的优生学还停留在人类表型特征阶段,鼓吹者和执法者对于真正的遗传规模要么一知半解,要么干脆进行曲解。
在政治运动和公众情绪的推动下,优生学运动成了社会风潮,并最终催生了纳粹政权所推行的「种族清洗」行动。
从 1933 年到 1943 年,大约有 40 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而仅在 1941 年,纳粹就用安乐死消灭了「没有存在价值的」 25 万成人和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