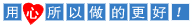近三年生物医药强劲的发展势头,让乐观的观察者好奇: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创新药、原创药的研发制造,能否追随美国在80年代的发展趋势,催生出一个千亿美元的产业?联系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进展,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又能否像人工智能领域一样,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两方面比肩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之一?
一直以来,相比于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并不属于硬科技领域的热门关键词。然而在过去三年中,它“悄悄”成为投资风口,稳居一级市场投资金额行业分布的前三。
根据清科私募通2017年公布的医药行业投资报告,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医药行业的投资额在2015年从92亿(2014年)猛增至233.12亿人民币,2016年为232.26亿。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人工智能领域2015年峰值时的159.50亿人民币,同时超过IT,电信及增值业务,金融等领域。在医药行业细分投资领域之中,生物制药占比最高,2016年占据投资数的29.2%。与此同时,对医药行业进行股权投资的投资机构数量也快速增加--从2014年的113家骤增至2015年的221家与226家。
生物医药行业在过去三年之中低调起飞和国家一系列改革、加快审批流程的政策变化不无关系。201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批制度的意见》,2016年《解决药物注册挤压实行优先审批的意见》,2017年《关于深化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将新药审评的案件挤压数字从 2015年22000多件减少到3000多件。CFDA又在2017年12月11日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将新药临床申请的批复缩短到90天以内。新药审批流程的加快,大大提升了企业新药研发的积极性。拥有新药产品线Pre-IPO阶段的药企,成为了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的明星。
众所周知,因为其极高的技术壁垒,极长的研发审批周期,生物医药产业对于创新研发能力和资本的抗风险能力都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在众多高科技创业投资领域中,生物医药产业也可说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然而近三年它强劲的发展势头,让乐观的观察者好奇: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创新药、原创药的研发制造,能否追随美国在80年代的发展趋势,催生出一个千亿美元的产业?联系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进展,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又能否像人工智能领域一样,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两方面比肩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之一?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美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飞,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成为全世界生物技术产业毫无疑问的“领头羊”。当今的基因工程药物多数源自美国,全世界的生物科技公司,美国占了三分之二。
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起飞并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增长,它还伴随着一种全新的新药研发和经济组织形式的诞生——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恰恰很好地解决了该产业在创新研发和资本投入上面对的种种难题。对照美国经验和现今中国资本市场与生物医药产业的现状,笔者认为,有三大隐忧可能会在未来阻碍产业的进一步起飞和持续发展。
隐忧之一:创新网络能否建立
当谈到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研发能力时,多数人会强调药企的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不够。发达国家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可以达到20%左右,而截至2016年底,我国的238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之中,研发支出最高的恒瑞医药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也不过10.68%,65%的上市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都在5%以下。
大型药企研发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创新药开发后劲不足。许多观察者指出,目前上市公司的新药产品线中,有许多并不是真正的创新药,而是针对同一靶点、分子结构类似“Me-Too”类药。生物制药行业赢者通吃。,比于真正的创新药,“Me-Too”类新药尽管拥有专利,但并没有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真正技术壁垒。
毫无疑问,大型药企目前是我国新药开发的主力军。其研发能力的不足,对行业发展有重大的阻碍作用。然而组织研究亦指出,大型企业内部的创新有着组织惰性、激励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一个行业要有持久的创新和发展能力,就需要其它创新主体的有力补充。
在美国的生物制药行业,大型药企并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在大型药企之外,另一个更专注、更有颠覆性、战斗力更强的创新主体是小型生物技术创业公司。这一类公司星罗密布于硅谷、波士顿、圣地亚哥的知名大学外围,由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博士们建立。这些公司打破了大学实验室和创业公司的界限,将实验室里诞生的前沿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快速开发。
得益于成熟的资本运作,很多创业公司还没有产品时就已经估值上亿美金甚至已经上市。当技术和产品发展成熟,它们很多会得到大型药企的战略投资或收购,利用后者的临床测试线和审批经验跑完新药研发最后最艰难的一棒接力。由大学、公共研究机构、风险资本、生物技术创业公司、大型药企构成的错综复杂、紧密联系的创新网络,解决了新药研发当中既需要颠覆性的创新能力,也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的问题,利用了创业公司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优势和大型药企的资源优势,的确是一种最优的组织安排。
回看中国,能否构建起这样的创新网络是生物医药领域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笔者认为,有两大结构性问题,在未来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网络形成的制约性因素。
隐忧二:大学能否成为创新之谷
美国生物医药行业自1970年末的起飞,起源自分子生物学的重大突破。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大学是毫无疑问的创新之谷——从7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引领行业的技术,都是从大学里诞生的。可以说,具备行业颠覆性的科学技术不从大学当中有效地转化出来,资本和企业再怎么厉害,也不可能带来一个千亿产业的起飞。
那么中国的大学做的怎么样呢?从论文来看,自2000年之后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论文发表仿佛坐上了特快车——根据自然指数2016年的统计,中国在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上已仅次于美国,在论文发表的绝对数量上更是已经超越美国。然而,根据新南威尔士大学Johann Murmann最新在中国管理学年会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来看,比照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在欧洲授权的专利,尽管绝对数量在上升,中国在医药制造领域的专利相对影响力在2000年之后就一直在下降。可见,尽管基础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在持续上升,具备商业转化价值的科技成果并没有相对应地增长。
除了可转化的科技成果欠缺之外,大学内部的一系列体制性因素也使得技术成果的转化困难重重。美国经验显示,对于科技成果最有效的转化需要发明人持续地参与后期的研发过程,甚至直接创办生物技术创业公司,或在公司中兼任顾问或技术总监等重要职务。而在中国,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化等制度上的障碍之外,大学的评价和激励体系也并不利于技术转化。对于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发表以及以发表为基础的学术奖项、头衔。学术竞标赛的激烈竞争占据了大部分科研人员的主要关注点。从教育部的角度来看,尽管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总体上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对于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离岗创业依然相当谨慎。
隐忧三:早期项目能否得到风险投资
除了大学技术转化困难这一结构性问题之外,另一大结构性问题是:目前创新药领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临床后期,临近上市前,对于早期的新药研制项目投资依然不足。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骆燮龙曾公开批评说,投资创新药“报个团玩玩”的心态不可取。新药研发在临床前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也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和判断力,极少有基金看得懂、敢于投这个阶段的项目。创新药早期的投资不足,阻碍了有潜力项目的诞生。
究其原因,和中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资金的机会成本有很大的关系。相较于美国,中国的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更高,因此股权投资的资金成本本来就高。近些年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快速发展迭代,使得风险资本能够快速获得高收益。这就抬高了生物医药领域的早期投资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人民币基金的期限通常是5-7年,短于传统美元基金。退出压力使得投资机构也青睐能够快速退出的后期项目。
创新药早期的高风险也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专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八十年代的美国,风险投资人的固定功课是阅读相关领域的最新论文,蹲守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学术会议上捕捉下一个能带来超额收益的新药。重组DNA技术的发明人之一、HerbertBoyer教授更是被风险投资人BobSwanson软磨硬泡,才一同创立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最具标志性的创业公司Genetech。中国投资机构多数是在近三年才开始关注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开始有专攻这一领域的投资人,有一定的技术和投资经验的积累。能否快速学习,积累足够的专业能力来降低生物医药领域早期投资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的投资机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