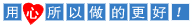阿基米德有句很著名的语录,“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如果有人把这种自信带到制药领域,说“给我一个靶点,我能成功开发出一个新药”,恐怕会招来一片质疑。对阿基米德来说,支点的选择举足轻重;对药物开发人员而言,选择合适的靶点也至关重要。
GPCR,中文名称“G蛋白偶联受体”,是人体中最大的膜蛋白家族,大约有800多个家族成员,现阶段可成药的靶点约370个,是人体内最大的成药家族蛋白,涉及的疾病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炎症等。《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2017年10月在线刊登的一篇文章数据显示:FDA共批准以GPCR为靶点的药物475种,占所有批准药物的34%。针对GPCR蛋白的候选药物在I、II 、III期的成功率依次为78%、39%、29%,成功率略高于针对其他靶点开发的药物[1]。
不过在这些被FDA批准的靶向GPCR家族蛋白的药物中,几乎都是小分子化药和低分子量多肽类药物。GPCR抗体药物难道是被医药界遗忘的瑰宝吗?显然没有!就在5月17日,FDA批准了第一个靶向GPCR家族蛋白的抗体药物Aimovig (erenumab-aooe)上市。这款由安进/诺华开发的靶向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的单抗药物不仅填补了美国市场GPCR抗体药物的空白,甚至被乐观人士分析销售额峰值可突破百亿美元。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去年7月在线刊登的一篇文章展示过GPCR抗体的开发前景和市场机会。记者从这篇综述中发现了一家中国生物创新药企业的名字——鸿运华宁(Gmax Biopharm)[2]。为此,记者在5月的一个下午专程来到距阿里巴巴滨江园区仅1公里远的鸿运华宁(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探索这家“十年如一日”专注于GPCR抗体药物开发背后的人和事。
缘起
景书谦博士曾在安进从事新药发现和药物开发14年有余。十年前,他离开这家当时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准备回国创业。几经辗转周折,景书谦在2010年遇到了愿意帮助自己实现愿景的合作伙伴,并在杭州成立了鸿运华宁,寓意“鸿运济世,华夏康宁”。
彼时,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不久,但生物制药的势头并未消减。从1997年首个人源化抗体药物(注:利妥昔单抗)的出现,到2008年已经有30多个抗体药物相继上市。科学家们纷纷将眼光从胰岛素等多肽类药物转移到单克隆抗体这类药物。
景书谦也想在抗体药开发上取得突破,但他不愿一味追随当时的热点或者只是跟随大药企的步伐。2008年,他从众多已经上市的单抗药物中窥到了一个机会。景书谦发现,已上市的抗体药多是针对EGFR、HER2、VEGFR等细胞膜表面的靶点。GPCR家族蛋白靶点虽然成药率较高,但全是小分子或多肽类药物,这是由于GPCR蛋白的结构复杂性,要获得针对该靶点的抗体药在当时仍属于未被攻克的世界性难题,因此FDA此前一直未批准任何GPCR抗体药上市。景书谦隐约感到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历史机遇。
他首先想到了曾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学弟张成,后者在GPCR的药物开发上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2010年的夏天,景书谦把张成博士约出来聊天,说出了自己即将回国创业的想法,并邀请他一起参加。
张成当时对国内的创业氛围并不是太了解,略显犹豫。直到一年后,当鸿运华宁在杭州的实验室已经建成,基本的仪器设备也都到位。景书谦再次向张成发出了邀约。这一次,经过慎重考虑的张成欣然应允。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张成直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师兄景书谦的敦促和国内创业氛围的感染,让我下定决心回国,也希望有机会做出治疗重大疾病的新药。”2011年年底,张成说服了家人,不远万里只身来到杭州,加入景书谦的创业团队。
与张成不同,自称“土鳖”的郭勇则是举家从成都东迁杭州。郭勇曾经在华神集团、康弘药业从事创新药研发及管理工作,众所周知的“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正是其在康弘药业作为核心研发人员全程参与近10年的项目,目前则担任公司副总裁,负责产品的海内外注册及临床试验和产品开发项目管理工作。
“我也是偶然了解到鸿运华宁开发的抗体药是从靶点就开始创新,而当时国内大多数从事生物药开发的企业都是做me-better类改良式的创新。”郭勇告诉记者,“具备源头创新能力的抗体药物研发公司在中国凤毛麟角,受到景博士的感召,感觉自己以往积累的新药研发经验与现有团队互补,对鸿运华宁的发展可以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就与家人商量,把家搬到杭州加入团队。”
鸿运华宁的药学副总裁范克索博士则是在2015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被公司的研发策略所吸引,遂于当年8月份加入公司。范克索之前在健赞、罗氏、Waters、BM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知名药企和机构工作了超过15年,回国后一直在友芝友从事双抗药物研究开发,熟悉生物药品的质量分析、工艺开发和临床申报。现阶段在鸿运华宁主要负责筛选更多高表达细胞株以及CMC方面的工作。
记者获悉,鸿运华宁现有75名员工,博士及海归人才近30名。但景书谦表示,人才梯度建设还远未达到他的预期。除了在药品开发管线上补充合适的人才,企业治理方面也是比较开放的。就在5月初,曾先后担任中美冠科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职务的朱秉先生也加入了鸿运华宁。
“做创新药好比开新式餐厅,靶点开发就好比食材的挑选,药物开发就像是烹饪厨艺的塑造。好的厨师对好食材必然要熟捻于心,但每个人精力有限,即便是好的厨师也未必精通餐厅的管理、服务要素以及菜品的包装等等。制药是一项系统工程,整个链条上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人才加入”,景书谦做了个简单比喻。
从鸿运华宁的高管名单不难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年龄层次分明、产业化经验高度互补、土洋文化背景互相融合,凝结成一个稳定而高效的运转体系。
此外,景书谦和张成皆提到,在安进工作积累的思维方式和国际化视野对鸿运华宁的研发管理工作大有裨益。譬如在安进工作期间,研发团队每周五有个happy hour的习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并将讨论结果制成的思维导图,最终成为某些试验技术路线图的雏形。如今,他们把这种工作习惯和氛围带到了鸿运华宁。
策略
2011-2015年间,基于GPCR家族蛋白靶点开发药物的销售收入总额接近9000亿美元。比较有代表性的重磅炸 弹药物包括高血压药物缬沙坦(AT1R)、多发性硬化症药物芬戈莫德(S1PR),糖尿病药物利拉鲁肽(GLP-1R)等。
景书谦从创业开始就将靶点锁定在作用机理成熟且成药率较高的GPCR家族蛋白上面。而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张成,其主要任务就是挖掘出适合制备成单克隆抗体的GPCR家族蛋白靶点。
熟悉GPCR家族蛋白的人都知道,GPCR拥有7个跨膜区,结构生物学分析很难进行,而且天然表达率极低,想要获得具有生物学活性的可溶性GPCR抗原极其困难,而抗原又是激发动物获得免疫产生抗体的必要物质。因此,早期的抗体筛选过程非常困难。
像大多数创业公司一样,鸿运华宁刚开始几年的道路也是艰辛和寂寞的。创业初期,即便是周末或者晚上,张成皆与他的这位学长同行。时而讨论实验方案,时而分享文献观点。白天则穿上白大褂穿梭于摇瓶子和养小鼠的实验室之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攻克了GPCR抗原制备、功能性抗体筛选等世界性难题,建立了一个可以高效筛选制备GPCR抗体候选药物的技术平台。景书谦和张成结合多年的药物研发经验,在370多个GPCR可成药靶点当中,首先选择了GLP-1R和内皮素受体ETa这两个兼具成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靶点确定为初期开发方向,并成功获得候选抗体分子。GLP-1R领域已经诞生了以利拉鲁肽、度拉糖肽、索马鲁肽为代表的多个重磅炸 弹药物,不过目前前尚未有GLP-1R抗体药上市,而鸿运华宁针对内皮素受体的抗体药更是世界首创。
在确定靶点后,又经过了2年多的工艺改进和优化,鸿运华宁筛选到了能制备出2~3g/L表达量的细胞株。期间,郭勇和范克索的先后加入高效推动了鸿运华宁基于这两个靶点开发的候选分子的药学、药效学、药动学及毒理学等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为临床试验的申报和开展准备了充分的前期数据。
“我现在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花在项目进度管控方面,”郭勇告诉记者,“没办法,新药开发就是这样,患者在和时间赛跑的同时,药企也是在赛跑,我必须盯紧点。保证质量、保证进度和成本控制是我工作的重心。”
郭勇自2015年2月加入鸿运华宁开始,就紧锣密鼓地筹备临床试验的申报工作。在当时,从细胞株构建到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准备好临床申报资料,再到递交CDE,平均需要18个月,再加上国内审评审批时间,一般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进入人体临床试验。2016年4月,鸿运华宁GMA102的第一项临床试验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启动,前后历时仅14个月。高效项目管理结合澳大利亚的国际化临床申报策略,使得鸿运华宁比国内常规流程研发的抗体新药项目提前10个月获得宝贵的人体试验数据。
“靶向GLP-1R的候选分子(GMA102/GMA105)已经进入Ⅱ期,在与艾塞那肽和度拉鲁肽的头对头试验中显示出了更好的降糖和减重的效果,心血管获益效果也得到了证明。”景书谦告诉记者,“不过,借助于美国孤儿药政策的优势,已经在澳大利亚完成Ⅰ期临床的靶向ETa的候选药(GMA301)却可能率先上市,我们正启动中美双报策略。”
GMA301的首选适应症是肺动脉高压,于2017年1月获得美国FDA的孤儿药资格认定。在美国,孤儿药可以享受一系列政策优惠,如美国临床试验50%的课税津贴、约200万美元的PDUFA费用免除、7年市场独占权等。今年5月下旬,卫健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也将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列为罕见病范畴。GMA301作为国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助课题,在后续开发中可以享受到一系列政策支持便利,这也有助于GMA301的后期开发和市场开拓。景书谦表示,GMA301有望在2021-2022年获得药品生产批件进入全球市场销售。
格局
德勤最新的数据显示,一个新药的平均开发周期为14年。鸿运华宁成立8年,目前开发了2款候选药物,启动了3项临床试验,进展最快的已到Ⅱ期临床。其中1款候选药获得FDA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此外,鸿运华宁打造了2个抗体制备平台,研发管线中的候选项目10余个。
作为一家技术、团队、执行力都属业内一流的企业,鸿运华宁要想成为中国创新药领域的翘楚,会不会有其他瓶颈?笔者对此的担忧是相比国内的其他创业者,景书谦开始的时间稍微晚了几年。那么如何跳出自身局限,推动企业的发展?
景书谦对此回应称:“除了在用人策略上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之外,鸿运华宁虽然仅成立8年,但已经做好了未来10-15年的产品规划。尤其是在开发第一代产品的同时,启动第二代、第三代产品的开发。以公司的两大抗体开发平台GPCR平台和Bibody平台为例,前者能用于动物的有效免疫且具有稳定高表达特点,克服了抗原制备以及会筛选出非特异性结合的抗体的难题,提升了抗体筛选效率。Bibody是一种不止于“双头抗体”的模块化平台,可以实现一个药物分子同时对两个信号通路进行调控,公司未来3到5年的申报项目将大部分出自此平台。”
显然,景书谦的创业之路首先是建立在对于技术、市场、团队、管理等各方面的理性认知之上的。不过新药开发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最终的成功上市还需要景书谦及其团队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张成的工作是一项承压极重的工作,一方面他需要通过不断设计,反复试验来发掘合适靶点,另一方面,他需要通过各种测试来鉴别成药率高的靶点,并决定是否需要推向临床前研究及后期临床。
对此,张成也保有一种科学家特有的乐观。“与大企业相比,最初的创业条件确实比较艰苦,能不能做出来也是个未知数。但哪个试验会100%成功呢?失败了就重新再做一遍嘛,最后筛着筛着就真的做出来了”,张成笑言道。
无论如何,对于开发一款中国自主研发的新药,景书谦和张成都抱有巨大的憧憬。景书谦略向记者坦陈,“上世纪80年代我国生物技术发展的确比较落后,但30余年过去,能让世界公认的中国研发的生物药依旧凤毛麟角。华人在外企做出的成果再多,这些药物反馈给国内患者的时候,刻上的都是“进口药”的标记,中国人就需要付出更高的用药成本。”
岁月
景书谦办公室墙上摆了诸多照片,大部分是与家人团聚的,另外一部分则是类似同学聚会的留念照。记者也是在一幅集体照中看到了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与一个重要的项目CUSBEA关联。
CUSBEA,全称“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从1982年8月派出第一批55位学生,到1989年派出最后一批49位学生,CUSBEA共选拔422位学生赴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景书谦是在1983年通过该项目来到UCSD攻读研究生。
如今,这些同学大多驰骋在生物医药相关领域,譬如大家熟悉的王晓东院士,余国良博士……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在国外都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收入的留学人员,如今大多数已经回到国内,继续从事药品开发相关工作。
为什么呢?景书谦坦言,创新药开发涉及的面比较广,一般得要有数十年的全产业链经验才能摸透行业,这并不是凭空就能喊出来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因为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而贪图享受,可能会使药品开发的基石出现断层,对整个产业发展显然弊大于利。
景书谦犹记得,他的课题是在母校UCSD旁边的Salk Institude里完成的。后者是全世界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之一,有数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过。创始人Jonas Salk先生虽然没有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最早开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用以对抗小儿麻痹症贡献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诺贝尔奖。
景书谦感叹,虽然自己在国外也主导或参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甚至在BMS跟随导师做研究员期间创下了从准备写稿到刊登出版在《Cell》仅历时1个月的记录,但相比较真正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产品而言,过去的学术成果几乎不值一提。
“到了我这个年纪,该经历的也基本都经历了,挫折、失败、失意……;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也亲身见证了安进的高速发展轨迹。”景书谦坚信,“通过借鉴成功的经验,并找到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情,应该是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的。”
采访完景书谦、张成等人,记者不禁心生感叹:当年的CUSBEA项目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意义非凡。出于岁月和专业赋予的使命感,本可以在海边喝着咖啡陪伴家人而选择回国创业的海归并不是少数。他们的初衷,或许只是想做一些回馈祖国并造福世界的事情。
新药研发的高风险无须赘言。从0到1的征途充满无限机遇和想象空间,但也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陷阱或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虽然大家不断在畅想中国生物药的明天有多美好,其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或许只有极少数人清楚,每天与药物开发打交道的研究人员带着巨大的压力替咱们负重前行。因为,新药的成功开发,始终离不开特立独行且又脚踏实地、从无到有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