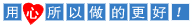听起来像个科幻恐怖片故事。2015年春天,一队科学家驱车来到广州的一个岛上,从装在卡车上的塑料罐里,释放了超过50万只蚊子。
这并非释放潘多拉魔盒,相反,科学家们放出这些打了“绝育药”的蚊子,是用来稀释种群密度。因为缺乏疫苗和有效药物,他们不得不以此遏制并阻断蚊子传播登革热的通道。
在中国,广东正是登革热多发和重点防控的地区,此前大多数年份,发病例数不会超过1000例。但2014年高达4.5万余例,是上一年总数的30倍。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过去的几十年间,登革热已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蚊媒传染疾病,遍及热带、亚热带128个国家和地区,威胁39亿人口。每年估计有3.9亿人感染,重症病人会严重出血,循环系统衰竭,并会有2.5%的患者死亡。
“登革热疫情在过去五十年增加了30倍。科学家们花了旷日持久的时间在研发登革热疫苗。”WHO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Bernhard Schwartländer)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旷日持久一词,用于登革热疫苗研发并不为过。20年、15亿欧元,折合近上百亿元人民币的付出,这还仅仅是法国药企巨头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一家的研发过程。
不过,“收获果实的时候已经开始。”施贺德博士说。2015年12月9日,这一天,由赛诺菲研发的全球第一支登革热疫苗在墨西哥上市。2016年1月,菲律宾和巴西也相继通过审批。这一严重威胁全世界数千万人健康的疾病即将得到遏制。
根据墨西哥和其他9个参与临床试验国家的数据,如果9-17岁人群的免疫接种率能够达到90%,5年时间里登革热的医疗负担可能降低50%。
着眼未来的疫苗
“这(疫苗研发)是一场艰难而又漫长的旅程。”负责第一支登革热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的法国科学家Wartel博士(T. Anh Wartel)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和许多传染病一样,人们一开始低估了登革热的严重性。尽管威胁人口众多,但制药先进的欧洲、美国几乎没有这种疾病,大部分制药公司也不愿意投大量资金去研发主要应用在这些国家的产品。像所有穷国特有的疾病一样,他们本国没有研发能力,无力承付疫苗和接种的费用、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尽管无药可治,疫苗研发也鲜有人问津。
但很快,随着城市化和地区间人口流动增加,疫情在全球不断升级。科学家们意识到,“几十年后这会成为全球威胁,也包括欧美。”埃博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该病毒当时仅出现在贫穷的非洲国家,疫苗研发缺乏动力,直到2015年,演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威胁。
作为一种经济又有效的预防控制手段,登革热疫苗的研究历史可追溯到1920年,研究者尝试从感染的埃及伊蚊体内分离病毒研发灭活疫苗。但由于登革热病毒血清型多、致病机理复杂,研发起来困难重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赛诺菲巴斯德专门组建研发登革热疫苗的团队,开始了新一轮攻坚。在内部,他们把这称为“着眼未来的疫苗”,主要为满足不同人群尚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联合疫苗、院内获得性感染、新型传染病等)。
登革热疫苗的研发非常复杂。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解释,登革热病毒因其抗原不同而被分为四种血清型,抵御其中一种血清型的抗体并不能保护机体抵御其它血清型病毒的感染。实际上,登革热病毒往往会通过第二种血清型来增强其感染,这个过程称为“病毒感染的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连续感染会增加个体患登革出血热及登革休克综合征的风险,还有可能发烧、呕吐及循环衰竭等。
Wartel博士证实了这一点。她回忆,他们上世纪90年代就和泰国玛希隆大学合作开发第一代登革疫苗,并在2001年证明了四价登革热减毒活疫苗的概念。但在2004年,因血清型3的反应原性和减毒效果不理想而失败。
“这非常具有挑战性。”WHO的施贺德博士说,“许多公司都放弃或搁置了登革疫苗的开发。”
但赛诺菲巴斯德始终在寻找“理想的登革热疫苗”,即一次免疫能同时预防4个血清型的病毒感染(四价疫苗),且4个血清型之间的免疫反应均衡,不存在加重疾病的潜在风险。
“公司和团队都没有想过彻底放弃,我们希望全球所有存在登革热问题的地区都能够获得安全有效的疫苗,无论他们身居何处。”Wartel博士回答,尽管历经波折,甚至几次中断,但项目始终存在。
进入二十一世纪,WHO监控到登革热疫情从热带、亚热带地区已经开始向北迁移。各国政府和援助团体终于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一连串旨在测试药物和疫苗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赛诺菲巴斯德也开始第二代疫苗研发,与此同时,阿坎比斯公司(Acambis)开发了基因重组疫苗技术,包括针对4种登革热血清型的四价登革热疫苗。这直接帮助这家公司走过了“生物科技死亡谷”——大部分风险资金是研发数年后才会进入,初创生物公司早期往往会经历缺少资金无法持续的挫折阶段,其中40%至50%的企业会死掉——但赛诺菲巴斯德收购了他们,重组新的团队,开始了进一步研发。
登革热的研发团队约有2000人,分布在不同国家。研究人员利用减毒黄热病毒(和登革热病毒同属)的疫苗株17D为载体,嵌合登革热四种病毒,变成嵌合病毒株,这些病毒株不会导致疾病,也不会通过蚊子传播,却可以引发人体的免疫反应,预防疾病。
但在证明对人体有效之前,需要动物模型的验证。赛诺菲巴斯德高级医学事务总监舒俭德博士说,理想的动物模型应该能够模拟人自然感染的临床表现,包括病毒血症、发热、血小板减少、出血等。大多数药物试验都通过大(小)鼠模拟,但对登革热病毒来说,这些非人灵长类动物并不能表现出人感染登革病毒后的临床症状,只能有抗体反应。
2009年12月5日到2010年12月5日,Sanofi Pasteur主持的临床IIb期试验在泰国4002名4-11岁儿童中开展。疫苗接种时间为0、6、12月,共3针。结果显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在受试者中产生四种血清型抗体。2014年,该疫苗成功完成III期临床研究,进入审批阶段。
因为登革热疫区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不同于以往所谓的旅行疫苗——富裕的西方人先获得疫苗而疾病流行人群最后获益的常规途径,赛诺菲公司希望疫苗能够直接进入疾病流行国家。
墨西哥是第一批受理的国家之一,其他登革热流行国家的审批也正在进行。赛诺菲巴斯德已向二十多个国家提交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覆盖人群达到10亿,但中国除外。
2015年10月22日,云南西双版纳,自8月15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发现首例登革热感染病例以来,武警云南总队西双版纳支队每天派出官兵协同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开展防疫消毒工作。(东方IC/图)
疫苗研发需要前瞻性
“我们一直认为登革热是输入性疾病,对中国影响不大,没人想到会有2014年的大爆发。”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主任罗凤基说,这些年他始终在监测各种传染病的进展。“但实际上它(登革热病毒)已经本土化了。”
在任何一种疫苗的研发中,对流行病学监测数据的掌握都是必要条件,往往也是评判一国研发能力的重要因素。康希诺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宇学峰曾在赛诺菲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当时公司决定花大力气投入到登革热疫苗中,就是基于对疾病流行和发展预测的数据都有很强的掌握。但即便如此,Wartel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审查候选国家时也大费周折,“很多落后国家缺乏有效的流行病学数据,大部分病例依赖临床诊断,且经常和其他疾病混淆”。
中国的疫苗研发,遇到的正是同样的问题。“最困难的是掌握疾病流行的趋势和整体评价,但问题是中国的流行病学数据不清,基础研究不足。”疫苗企业北京科兴生物公司总经理尹卫东说。
“疫苗生产周期较长,任何限定时刻的产能都是固定的,无法扩大生产,建立新的生产设施需要花费四到六年的时间。”宇学峰说,因此,好的疫苗企业需要有强大的预测能力和前瞻性。而这正是中国同行被诟病的问题所在。
科兴生物曾研发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但过程,无疑比国外同行要难得多。
尹卫东说,研发过程中,他们需要去不同的城市采样,自己做病原分析、流行病学分析和病毒学研究。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通常是由卫生、疾控和大学分工协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有一项专门针对小公司的合作计划,名为生物防御合作(Partnerships in Biodefense)的计划,推动研究人员与公司的合作。“如果我们等数据足够再研发,等得了吗?”他反问道。
而另一方面,疫苗研发的耗资和风险也非常巨大。据了解,大的跨国药企研发投入通常在15%左右,每年高达50亿欧元。企业一旦定下项目,会坚定地执行下去,终止项目一般是从项目质量上考虑,而不是方向和资金原因。而中国企业绝大部分研发投入在5%以下。
舒俭德博士总结了新疫苗研发投入的三个“10”——疫苗的平均研发投入超过10亿美元,要花超过10年时间,但只有不到10%的成功率。以赛诺菲为例,他们曾在1995年到2006年花了十多年时间研发癌症疫苗,但最终这个项目因为前景不佳而被停掉,投入的三个多亿美金也打了水漂。
相比之下,国内企业更愿意做国际成熟的疫苗品种。“我们90%以上都是仿制苗,三五年就出来,真正创新的屈指可数。”宇学峰感到遗憾。
但这并不代表国内企业技术不如国外,尹卫东觉得。一些例子是,中国的甲流、禽流感、EV71疫苗(预防手足口病)都是世界领先研发出来的。
“EV71疫苗从开始立项到最后用了八年时间,国家花了大力气和资金。”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员张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尹卫东公司的EV71的项目,政府就支持了七八千万元,占研发投入的五分之一。但他也坦言,其中一半时间用花在了新药评审上。
SARS和流感的爆发曾促使中国对传染病防控设施做出大笔投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关注点集中在国内需求上,而非全球性疾病。
问题在于国内企业现在根本无法满足本国需求,只能把精力投入到最迫切的领域。“美国3亿人口,他们可以生产6亿支疫苗,但中国所有的企业不眠不休也覆盖不了近14亿人口的需求。”尹卫东说。
尽管赛诺菲公司回复,他们现在无法告知该疫苗的价格。但据彭博社分析,到2020年,该疫苗一年的销售额将达14亿美金。但这个新疫苗能否在商业上成功,主要取决于登革热流行的亚洲和拉美国家政府推行的意愿有多大。除了赛诺菲,还有5个登革热疫苗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施贺德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WHO正在看第一支登革热疫苗的数据,评估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证据确凿,他们将会尽快出一份推荐使用指南,并计划如何推动疫苗的使用。大部分时候,这类疫苗会进入WHO的采购目录,以低廉的价格达到贫穷国家人民的手中。正如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Albert Sabin 博士所说,“放在货架上的疫苗毫无用处。我们必须确保所有需要的人能得到疫苗。”
据了解,中国至今仅有三个产品通过了WHO采购目录,无法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也是国内企业不敢贸然做新疫苗研发的一个原因。“主要是我们的标准和国际上有差别。”尹卫东不认为国内疫苗的品质不好。
“阻止病毒的最佳途径是从源头上阻止。一个安全、有效、可负担的疫苗将会极大地控制疫情,降低死亡率,减轻疾病负担。”施贺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