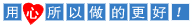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关于制药业创新未来的两种愿景。一个令人振奋,另一个则并非如此。
第一种是诺华(Novartis)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签署的200亿美元协议。该协议允许它们互换资产,从而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集中发力。第二种是Valeant向肉毒杆菌生产商艾尔健(Allergan)发起的460亿美元的敌意收购。Valeant是一家迅速发展的并购型公司,得到多家对冲基金的资金支持,由一位前麦肯锡(McKinsey)顾问经营。
就第一种愿景而言,大举投资于抗癌药物与疫苗研发的制药公司找到了不用大举并购就可以致力于最擅长领域的方法。就第二种而言,公司不断撮合交易,同时削减研发支出以节省现金并取悦华尔街,生产了用于治疗痤疮和足癣的新型药膏。
你倾向于哪一种?
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意义,因为制药业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该行业多年来生产率提高缓慢,回报率不断下降,过去并购而成的公司自顾不暇,不指望它们能帮上什么忙。治疗癌症和其他严重疾病的药物正在出现,随之而来的还有对交易的渴望和融资。
一些企业想要重启医疗业于2009年被迫终止的上一波并购潮,比如辉瑞(Pfizer)以680亿美元收购惠氏(Wyeth)。并购结果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但辉瑞并不畏惧,仍然提议以1000亿美元收购英国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诺华与GSK交易的美妙之处在于,它表明了利用精确和决心可以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像华尔街通常做的那样,将资产打包并给出高溢价,向顾问和银行支付大笔费用。交易双方都很慎重,而不是对什么都支付高价,包括不那么对症的药物。
诺华首席执行官江慕忠(JoeJimenez)表示:“大多数公司都有一些核心资产比其他资产更值钱。”收购方的对策是打散整个资产,然后拿走核心资产。这次交易让诺华放弃了疫苗业务,同时获得了GSK的大部分肿瘤业务以及一家生产消费药物的合资公司。
此类交易很难完成——你务必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就资产估值达成一致,签订适合双方的结构性协议,而且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完成。但是当完成这些交易时,比如像能源和食品行业做得那样,这些公司就会非常高效。
这些交易适用于制药公司,后者经常追逐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和药物,但它们会因专门经营而受益。它们并不热衷于出售规模较小的部门来获得现金,因为它们现金充足,但它们想要增强其规模较大的部门。资产互换远不如收购那样诱人,但同样也没有收购那么浪费。
我们因此开始关注Valeant。2008年,麦肯锡前制药业务主管迈克尔?皮尔森(MichaelPearson)出任Valeant首席执行官,自那以来Valeant发展迅速,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错过了它。但皮尔森不打算放缓公司的发展——他希望该公司到2016年能跻身医药行业前5名。由于Valeant依照业绩表现发放奖金,皮尔森如今已经是一位亿万富翁。
Valeant的业务模式非常简单,但其会计和税收结构非常复杂。皮尔森在麦肯锡的时候就断定,他为之提供咨询服务的这个行业是个烧钱的地方,这不只是指建造总部和聘请员工需要花很多钱,而且还有药品研发上的投资。聘请科学家研发新药非常“烧钱”,因为他们失败的概率很高。
当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时候,他将Valeant的研发支出削减到收入的3%——相比之下,大型制药公司的这一比例通常是19%左右——然后通过举债收购其他公司来获得产品。Valeant自2008年以来收购了逾35家公司,包括去年以87亿美元收购的博士伦(Bausch&Lomb)。
肉毒杆菌将会符合皮尔森的策略。他喜欢皮肤病和眼科等领域的知名品牌——在这些领域,买家是病人和医生,而不是对成本敏感的保险商和医疗体系。他计划将艾尔健的11亿美元研发预算削减9亿美元,并集中研发低风险项目。
他在这个合资企业的合作者是潘兴广场资本公司(PershingSquareCapital)的创始人比尔?阿克曼(BillAckman)。潘兴广场资本公司是一家主动型对冲基金,它迅速收购了艾尔健9.7%的股份。在本周的一次报告中,阿克曼将皮尔森比作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和《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前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Graham)等其他反传统的管理者。
如果格雷厄姆认为新闻调查是一项高风险低回报的活动,将《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室的大部分员工解雇,包括爆料“水门事件”丑闻的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然后购买电讯稿,那么这种类比就是成立的。但在现实中,她和巴菲特一样,从更长期的角度来投资企业。
皮尔森迄今为其股东和自己带来了巨额利润,如果Valeant和艾尔健整合后加大对肉毒杆菌变种(雾化肉毒杆菌?)的投资,而不是研发新型化妆用化学物,那它就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如果整个制药业都像他这么做,药品研发将会停滞。
制药公司的一条出路是强化对抗肿瘤药物等领域的研发,交换资产以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集中发力。另一条出路是屈从于对冲基金支持的削减成本的压力——对冲基金认为5年就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这是一个道德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