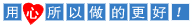生意社1月29日讯 1998年,英国皇家自由医院胃肠病学家安德鲁·韦克菲尔德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论文,称一些儿童在接种麻风腮(麻疹、风疹与腮腺炎)三联疫苗后,出现了自闭症症状。 虽然12年后,《柳叶刀》撤回了这篇数据造假的论文,韦克菲尔德本人被吊销行医执照,但这场骗局带来的影响远未结束。声势浩大的“反疫苗运动”席卷全球:法国有抗议者相信,接种肝炎B型疫苗会引起多种硬化症;在美国,人们误以为疫苗中的硫柳汞会导致自闭症;印度流传着儿童乙型流感疫苗会导致乙型脑炎的谣言;在南非,人们听信从英国漂洋过海来的谣言,拒绝接种疫苗而出现了一批麻疹患者。
如今,回头再看这些疫苗信任危机,专注研究日本疫苗赔偿法例的学者杜仪方颇有感慨:“疫苗是一个典型的风险领域,每个正常人,在不知道它全貌的时候,都会往最糟糕的地方去想。风险领域最强调的就是风险交流,只有相关信息得到充分披露,消费者才能理性去选择与面对。”
所有这一切的教训是,接种疫苗不应该是一个由家长为孩子作出的个人选择,它是个公共卫生问题
虽然事后看来,韦克菲尔德的研究论文连基本的随机对照试验都没有。“甚至不是科学的研究,只是一个小伙儿在描述一件事——12个孩子,里面9个觉得孩子有自闭症,其中8个孩子的家长记得症状是在疫苗注射不久后出现的。”2014年年初,一位普利策奖得主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用近乎痛心疾首的语调回顾此事,“这项研究已经是不列颠有史以来出版过最出名的科学论文之一,不过是声名狼藉的那种。”
“有些症状虽然是在接种之后发生,但与疫苗并没有因果关系,在医学上被称为‘偶合反应’。”上海疾控中心从事疫苗接种管理工作的陶黎纳解释。判断是否属于偶合反应的根据之一是统计数据。一般来说,要将接种疫苗人群与未接种疫苗人群的数据对照,通过两组数据出现的明显不同,才能看出疫苗的效果。
事实上,许多疫苗信任危机事件,就源自偶合反应。譬如席卷欧美的这场反疫苗运动,科学家后来分析称,自闭症或其他精神损伤性疾病通常在幼儿18到24个月大时开始显现,而这恰好也是孩子接种多种疫苗的时期。就像陶黎纳所说的那样,或许先后发生,但没有因果关系。
韦克菲尔德的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陆续有病理学者、生物学家宣称,在自闭症儿童血液和脊髓液中检测到麻疹病毒高抗体。2001年,首相布莱尔和夫人切丽拒绝透露他们19个月大的孩子是否接种了三联疫苗;谣言传到了法国,小孩只能接种麻疹疫苗。
当时,质疑这一“科学事实”以及任何捍卫疫苗的人都会遭到攻击。美国儿科医生保罗·沃菲特因公开宣称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疫苗并没有引发自闭症,而收到了恐吓信,甚至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镖保护。
然而论文发表12年后,被揭穿的是韦克菲尔德。原来,他接受了想要起诉疫苗公司律师的资助,擅自篡改病例,论文中提到的12个孩子有5个在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出现孤独症症状,还有3个从未有过孤独症症状。
但疫苗行业遭到重创。英国接种麻风腮三联疫苗的儿童数量锐减,2004年,该国疫苗接种率降低到80%,麻疹的发病率则直线上升。根据美国疾防中心的数据,该论文发表后,已有3名儿童因未接种疫苗而死于麻疹。
如今人们能清晰看到整整一代人降低疫苗接种的后果。在一张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公布的2008至2014年全球“疫苗可预防疾病爆发图”上,美国国土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百日咳疫情,而欧洲以及非洲密布褐色的麻疹疫情。
“所有这一切的教训是,接种疫苗不应该是一个由家长为孩子作出的个人选择,它是个公共卫生问题。因为未接种孩童罹患的传染病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看过了全球疫情地图后,《洛杉矶时报》老记者在报道中吼道。
疫苗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事件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会得到细致的监测和调查
如何在疫苗危机中恢复公众信任,对于卫生官员、科学家来说是个大难题。反疫苗运动阵营中,不乏各界名流:美国《花花公子》封面女郎麦卡锡和她的好莱坞明星男友金·凯瑞常常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疫苗造成的精神问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在《滚石》杂志撰文,把儿童疫苗中的汞含量说高了一百倍。“我们接受的训练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儿科医生沃菲特认为科学家应该更努力去赢得公众,“但为科学而战是我们的责任。”
如今,在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专门有一个网页来阐述“关于疫苗接种的传言和事实”,其中两个传言就是“疫苗含有水银”与“疫苗会导致自闭症”,WHO以“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中的硫柳汞用量会对健康构成威胁”、“没有证据表明麻风腮三联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回应了那一场轰轰烈烈、延续十余年的反疫苗运动。
相比之下,在美国疾控中心的官网上提供了与疫苗有关的各种资料,细致到每种疫苗接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症状,以及每一种症状出现的概率及时间,以供家长比对。
为了进一步做到公开透明,这个官网还有一个名为“您孩子的疫苗之旅”的网页,用简洁的数据图片说明了疫苗从研发、生产到监测的全过程:研发时会经过大规模的对照组实验,生产时会考虑不同年龄段等各种因素,而复杂的监测体系保证了科学家们能实时对疫苗效果追踪评估。
全方位、各阶层地开展公众教育是重塑疫苗安全的关键。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仪方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日本民间也曾兴起过对疫苗的怀疑。当时,接种牛痘而产生不良反应的案例出现在东京、大阪等多个城市。
面对这次疫苗信任危机,日本政府首先降低了疫苗的接种费用,原本应当个人承担的部分由政府来承担,同时,改变从前个人去医院接种的做法,变成让医生到学校与社区去接种,在经济、便捷度方面加强了人们的接种意愿;此外,很多关于疫苗的信息会在媒体上公开,药厂开放让媒体采访,社会可以去了解整个疫苗的生产流程与鉴定流程。
杜仪方看过日本政府拍摄的相关纪录片,片子记录了疫苗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中间怎样去抽取样本,怎样去鉴定,过程是否保持公正。有段时间,这部纪录片不断在电视台上播放。
如今,日本政府早已不再规定儿童的强制接种疫苗,可这并不妨碍疫苗接种率保持着高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要接种疫苗已经是家长们的一种共识了。”杜仪方说。
针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疫苗接种“恶魔抽签”,很多国家的政府致力于从保障补偿的角度予以补位
除了加强科普工作,完善的疫苗监测体系也是重塑公众对疫苗信任颇为重要的举措。美国的疫苗监测体系分三部分——首先是疫苗不良反应事件的报告系统;然后由疾控中心与若干医疗机构合作组成疫苗安全数据链,以监控识别确实因疫苗而引发的不良反应,最后是几大医学中心组成的研究机构,对疫苗引起的不良事件作临床免疫安全评估。
“没有一种疫苗是100%安全或有效的”,美国疾控中心网站将这句话广而告之。这种严重反应发生的概率,大约在100万分之1到2左右。在日本,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恶魔抽签”。接种的人数够多,就一定会有人被抽中。
针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疫苗接种“恶魔抽签”,很多国家的政府致力于从保障补偿的角度予以补位。在日本,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会得到不少补偿。杜仪方举例说,对那些因接种疫苗残疾的人,政府甚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会每年支付给当事人一笔足以治疗并弥补工作损失的补偿款。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发生过一系列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等疫苗引起不良反应的诉讼。为了避免药企因为巨额赔偿退出疫苗生产市场,美国在1986年出台《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两年后国会又根据这一法案通过了《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这是一个为了解决疫苗不良反应而建立的无过错责任体系,由联邦索赔法院、司法部以及人类健康服务部共同管理,赔偿范围涵盖了所有常规推荐的儿童疫苗。
被反疫苗人士视为恶魔的沃菲特医生,业余时间还喜欢研究人类的反疫苗运动史。他发现,近两百年来,人们就没在这个问题上消停过。
在19世纪的英格兰,尽管人们发现了牛痘可预防天花,还是有许多人拒绝接种。讽刺画家在杂志上为接种人士按上了奇模怪样的牛头,这些伟大的小册子作者们就像如今网络上一呼百应的名人一样有着超乎想象的影响力,“那是反疫苗运动的诞生,”他说,“到1890年,他们已经使免疫率下降到了20%的量级。”
运动结果是天花在英格兰的再度爆发。提起这段历史,沃菲特吸了一口气:“你想要相信,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对于疫苗恐慌,杜仪方也有了自己的看法:“作为普通家长并不知道疫苗从生产、监管、乃至接种不良反应后补偿的情况。但如果有一个疫苗审评的技术数据平台,把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反应,疫苗的监管、研发,包括它的临床试验结果公布在上面,人们能看到,其实只有100万分之1的不良反应概率,相比起人们光能从媒体上看到各种打疫苗后得病的消息,这要更让人安心。”
与美国疾控中心网站相似的一点是,她立刻就能从日本厚生省(相当于卫生部)的网页上查到各项疫苗的每年接种人数、发生不良反应的人数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