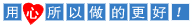“诊室备有辣椒水”,“调解室椅子固定”,在医患矛盾频发背景下,跳出公立医院密集门诊日程,选择自由执业的知名医师在增多。
100多位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一座孙中山雕像下无声集结,现场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沉痛哀悼温岭遇害同仁”。上海中山医院“巴林特小组”成员,和他们短暂离岗的同事,一起默哀了三分钟。
10月31日上午,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的追悼会举行。自25日事发起,当地官方不断通报这起伤医事件进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高度重视因医患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
默哀结束后,一位女医生泪流满面。她握住上海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的手说,“谢谢”。杨震在微博账号“快乐是一棵树”上说:我们表达哀伤,我们呼唤正义。
相似的场面令杨震记忆犹新。一年多前哈尔滨医生王浩遇害后,在中山医院紧急组织的巴林特小组心理讨论中,一位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女住院医向大家哭诉,她的室友听到消息,难过地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夜。
2009年9月这家上海著名的三甲医院引进“巴林特小组(BalintGroups)”。每两周活动一次。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精神分析师米歇尔·巴林特创建了这种训练全科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方法,它假设“潜意识在每个人心里,不仅是在病人那里”。
越来越能直接感受的医患纠纷,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曾连续五年在上海市卫计委负责医患纠纷调节的孙梅对记者说:到上海任何一家二级医院坐上一天,肯定会遇到医患纠纷。原卫生部2012年统计显示,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而2013年见诸报道的伤医案件已有20起。10月下旬连续发生3起医疗暴力事件。
“诊室备有辣椒水”
在医患调解室里,连热水瓶都不能放。经验还告诉他,甚至手表、手机等稍微值钱些的物什,也不能带进去。
温岭“10·25”伤医事件发生之后,从同属于台州的黄岩,到相邻的上海,乃至更远的地方,无数的医务工作者表达了他们的哀悼和声援。
案件发生第五天,巴林特小组活动的主题是“医路的爱与哀愁”。杨震对未来并不乐观,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医患纠纷一望无际”,但“我们必须到达彼岸”。
深圳市一名70后牙科医生,将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团漆黑。他在微信群里对初中同学们说,温岭伤医事件,比去年3月哈医大王浩案更“令人发指”。他觉得包括王云杰在内,医生和医院都是无辜的。
孙梅当年分工负责上海普陀区的有关工作,她遇到过最厉害的一次纠纷,48位家属一起前来。而创下上海之最的,是某次100多个家属围堵华山医院。
纠纷频发,医院不得不加强防护。孙梅回忆,当年医院里普遍专设一个谈话室用于医患沟通,在这个特殊的房间里,连热水瓶都不能放,以防激动的家属随手抄家伙伤人。
杨震感觉现在的情况有过之无不及。谈话室里椅子必须是固定的,也不能吸烟——只要一点火消防设施就会自动启动。经验还告诉他,甚至手表、手机等稍微值钱些的物什,也不能带进这个房间。
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琪介绍,两年前其同事徐文主任被患者砍伤,现在诊室里备有辣椒水,医师一旦有人身危险就会用。
温岭伤医事件三天后,10月28日,杨震受邀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演讲有关医患纠纷的应对技巧。他特意强调是“应对”而非“防范”——“根本防范不了”。
“医患冲突没有得到任何缓解,甚至还在加剧”,杨震说,长期顶着各种压力超负荷工作的医者需要自愈,而巴林特小组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治疗”。
“这么多年来,我并不恨任何一个‘医闹’”,杨震说他慢慢学会了包容和宽恕,何况疾病才是医生和患者的共同敌人。
密不透风的日程表
检讨一下,如果能再压缩难为情的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这样就能给每个病人3分钟了。
11月1日,上海一些医生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这样一段话——今天我7:20开诊,共看诊192个病人,到最后一个病人看完离开是17:18,一共是598分钟。出去四次上厕所共8分钟,中午吃饭10分钟,数次喝水耗时约6分钟,用于看病人的时间是574分钟,平均每个病人用时2.99分钟!检讨一下,如果能再压缩难为情的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这样就能给每个病人3分钟了——段子据传是以骨科诊疗见长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医师所写。
根据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引入的新加坡著名医疗管理集团百汇集团的标准,每个病人的首诊时间不能少于15分钟。去年底离开体制自由执业的原上海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医生,向预约病人承诺首诊不少于30分钟,复诊不少于15分钟。
密不透风的日程表,造成了医疗质量和医患关系的诸多隐患,这背后是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极度不合理,也是新医改致力改变,却收效甚微的地方。
即便如此,孙梅认为医生并不是无可作为,因为沟通中70%以上是情绪,医者的冷漠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孙梅告诉记者,自己前一周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就诊时,亲眼看到一位护士横眉冷对首次前来该院求医的江西患者,一连用五、六个“不知道”打发了关于专家出诊时间这样的基本问题。而五年的医患纠纷调解生涯使她相信,医者良好的态度本可以避免许多悲剧。
拥有257万粉丝的前协和医院急诊科大夫于莺在微博上表示,其实患者体验的医疗,从跨进医院第一步就开始了。冷暴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到医生那里达到高潮,直到爆发。“医生所受到的遭遇是在为患者遇到的每一个不如意买单。”
当年工作分工使然,孙梅经常出入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高干病房,“医护人员像对亲人一样”,“医界也要自省”,孙梅说。
自由执业转暖?
涉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推行自由执业完全改变现在的体制格局不太可能。
10月28日,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周乐今医生,参与联署了就医院暴力向公众发出的公开信,呼吁推行全国医院暴力“零容忍”。
和他一起联名的有正在台湾学习、准备将来自由执业的于莺,不久前跳出体制的民营上海德济医院院长宋冬雷,以及以“非典型医生”之名在微博上为医师自由执业大声呐喊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师张子谦等10位医生。
10月30日上午,周乐今又在一个讨论“医改”问题的微信群里,宣布了他最新的想法——进行自由执业的新尝试,个人开店,提供慢性心血管病管理方面的个人化服务。
他在微博中宣布,药品请到药店和医院自购。诊费合理,但绝不是公立医院专家号的“白菜价”。
对于在此时宣布这一消息,周乐今说得很直白:当今医疗体制下,政府才是医者的衣食父母,患者不是!当医师成为自由执业者,完全靠自身医技服务挣钱之时,医患关系就必然和谐了。
“反正我早已是‘先烈’了!”周乐今在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群里自我调侃。数年前,他率先挣脱体制,放弃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科科主任职务,受聘于民营医院,后一度陷入与后者的法律纠纷。
这段曲折使周乐今更坚定了自由执业的决心,有望摆脱受制于体制或受雇于资本的地位。迄今为止,周乐今的微博已被转发近千次。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指出,自由执业“解放”了医生,能够促进医疗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从而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朱恒鹏解释,自由执业不是说一定自己单独执业,而是说有选择执业方式的自由,包括是否当医院雇员的自由——自由的真正含义是有选择权,声誉机制和竞争机制,会让医生认真行医合理定价。
但他也指出,因为这涉及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推行自由执业完全改变现在的体制格局不太可能。朱恒鹏建议,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离退休的医师按照现行制度继续发放退休金,在岗医生保留国有事业编制身份及相应待遇。但从此取消国有事业编制制度,新人全部采用合同制,缴纳统一的社保基金。
“这样一来,医生不必再去争编制、争身份,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治疗技术和患者身上”,朱恒鹏说。